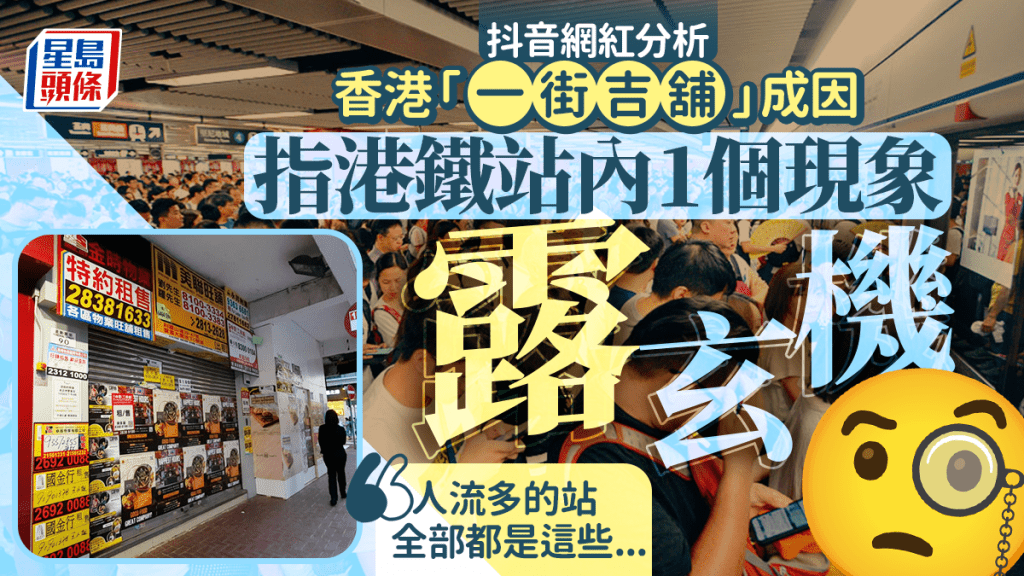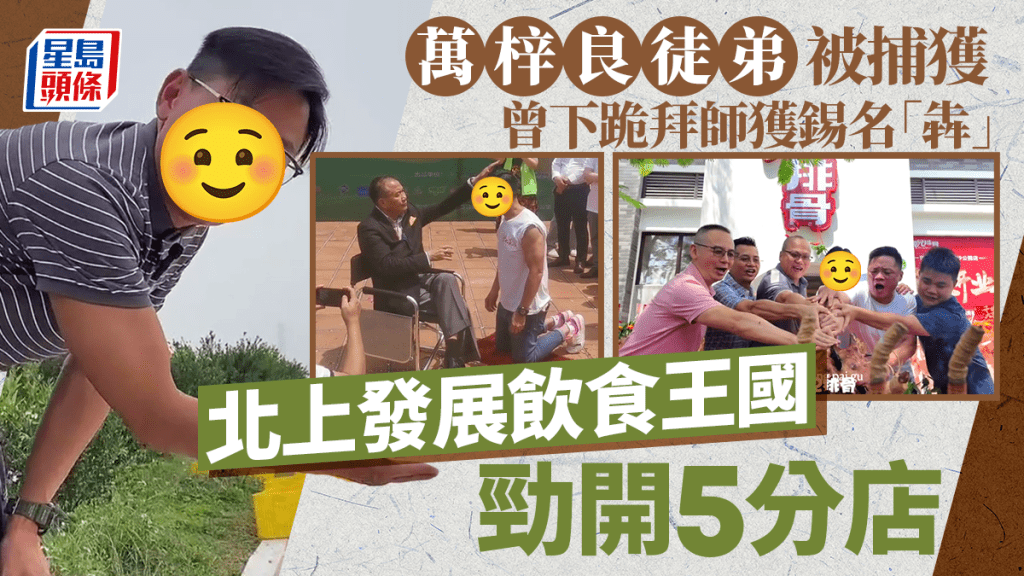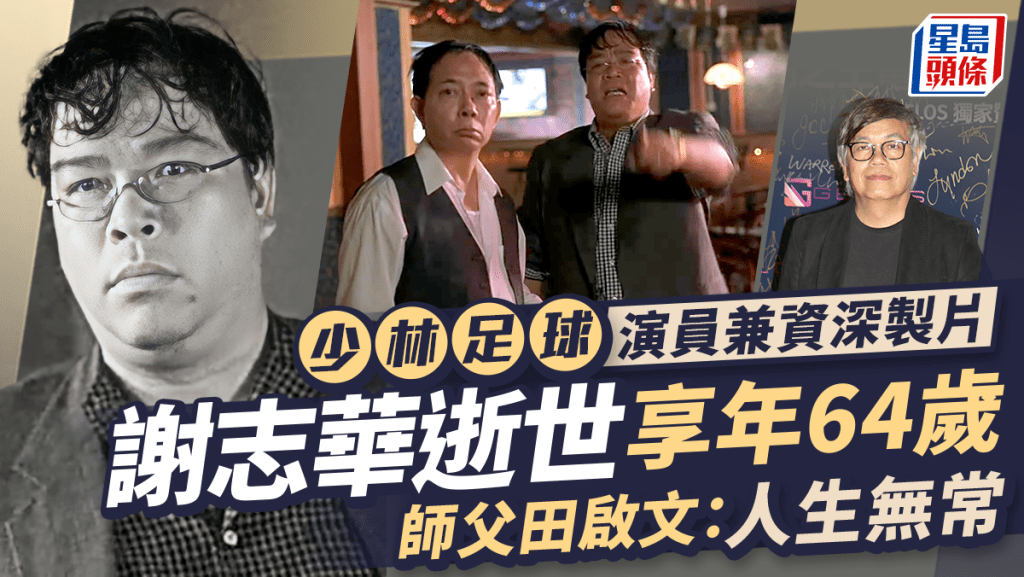無名指——像黃牧那樣生活
收到黃牧死訊那個早上,我好難過,好像有塊鉛塞在心裏。本來約好疫後北京再聚,他等不到免隔離通關就走了。
知道黃牧的人不少,但更多人認識他的筆名古鎮煌,那個最會「歎世界」的隱世高人。他說本想以「股王」作為筆名,怕太招搖,想到自己經常「搞搞震」,於是取「股震王」為名。
黃牧一向「招積」,曾自詡每月給股票經紀的佣金,比自己正職的工資更高,所以「索性唔撈」。我二十多年前認識他,他已提前退休多年,全力「食買玩」。那時我想,活到某個年紀,也要過黃牧那樣的生活。
美食、紅酒、名錶、鋼筆、郵輪、酒店都是他的愛好,這些他都以古鎮煌之名分享,唯有古典音樂(和後來的芭蕾舞)才用真名撰稿評論。
八九十年代,我每星期看《明周》就是為了讀鄭延益、高考亮和黃牧的音樂專欄。這三位前輩我後來都認識了,常有機會受教。鄭老師和高教父待我甚好,但他們都是「老師」和「教父」,唯有黃牧我才敢直呼其名。
黃牧於我亦師亦友,他音樂鑒賞力比我高得多,但從不以俯視角度與我交流,偶然還會把未出版的文章發給我先睹為快。很多人覺得他脾氣古怪,我卻和他相處得很好,近十幾年他周遊列國之餘較多在北京,我因工作之便也與他常見面,天南地北甚麼都聊,用他的話就是「亂噏一餐」。
作為樂評人他喜歡以「蓋棺定論」評價已故音樂家。如今他不在了,我斗膽也給他下個蓋棺定論,就四個字——不枉此生。
譚紀豪
知道黃牧的人不少,但更多人認識他的筆名古鎮煌,那個最會「歎世界」的隱世高人。他說本想以「股王」作為筆名,怕太招搖,想到自己經常「搞搞震」,於是取「股震王」為名。
黃牧一向「招積」,曾自詡每月給股票經紀的佣金,比自己正職的工資更高,所以「索性唔撈」。我二十多年前認識他,他已提前退休多年,全力「食買玩」。那時我想,活到某個年紀,也要過黃牧那樣的生活。
美食、紅酒、名錶、鋼筆、郵輪、酒店都是他的愛好,這些他都以古鎮煌之名分享,唯有古典音樂(和後來的芭蕾舞)才用真名撰稿評論。
八九十年代,我每星期看《明周》就是為了讀鄭延益、高考亮和黃牧的音樂專欄。這三位前輩我後來都認識了,常有機會受教。鄭老師和高教父待我甚好,但他們都是「老師」和「教父」,唯有黃牧我才敢直呼其名。
黃牧於我亦師亦友,他音樂鑒賞力比我高得多,但從不以俯視角度與我交流,偶然還會把未出版的文章發給我先睹為快。很多人覺得他脾氣古怪,我卻和他相處得很好,近十幾年他周遊列國之餘較多在北京,我因工作之便也與他常見面,天南地北甚麼都聊,用他的話就是「亂噏一餐」。
作為樂評人他喜歡以「蓋棺定論」評價已故音樂家。如今他不在了,我斗膽也給他下個蓋棺定論,就四個字——不枉此生。
譚紀豪
最Hit
紅磡殯儀館罕有公開請人 每週返一日 開價「咁多」 網民:比想像中低|Juicy叮
2024-10-23 13:56
前TVB小生晒近百萬新車被寸一輩子都買不了 多地置業獲封隱形億萬富豪高EQ回應
2024-10-24 12:3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