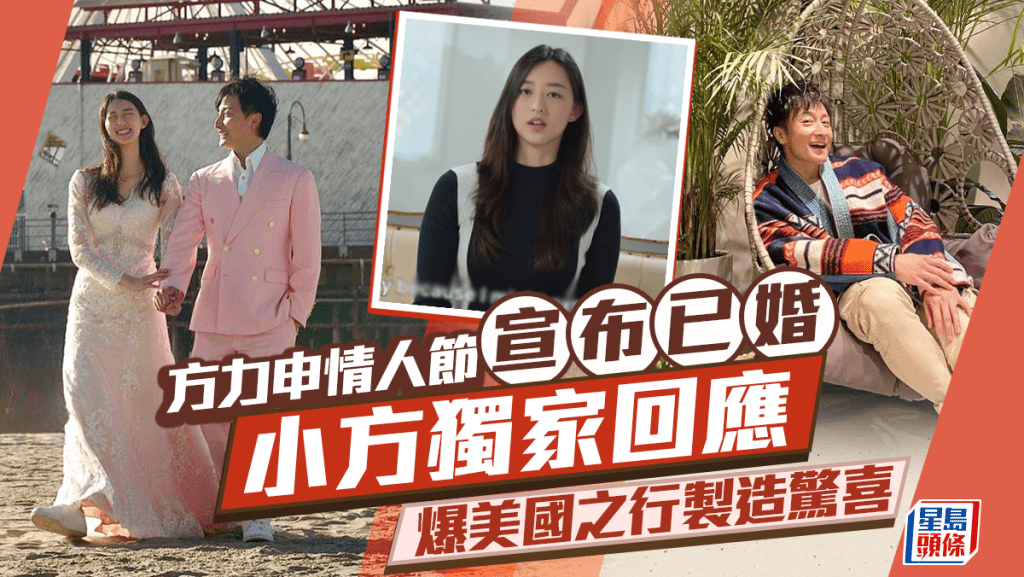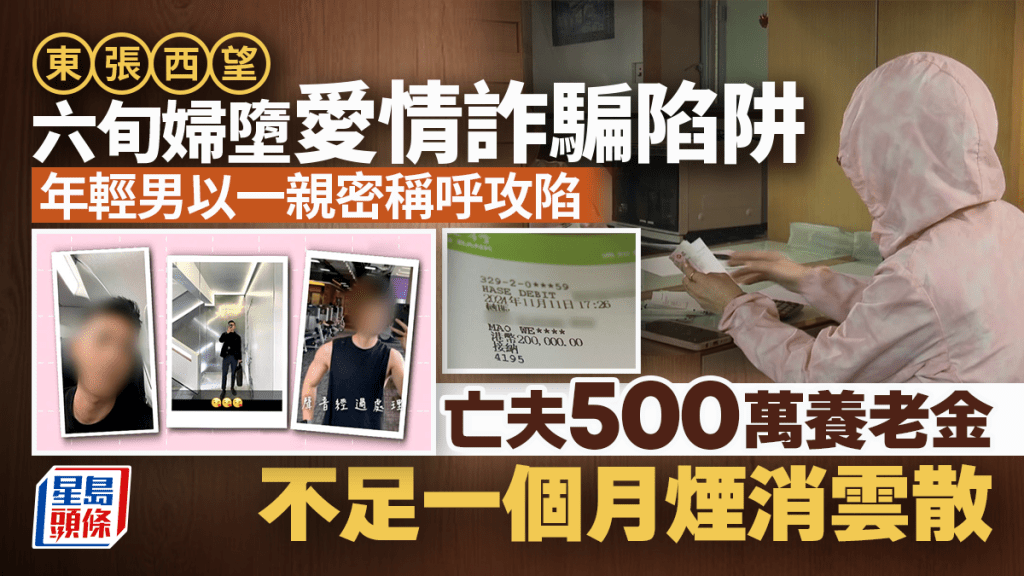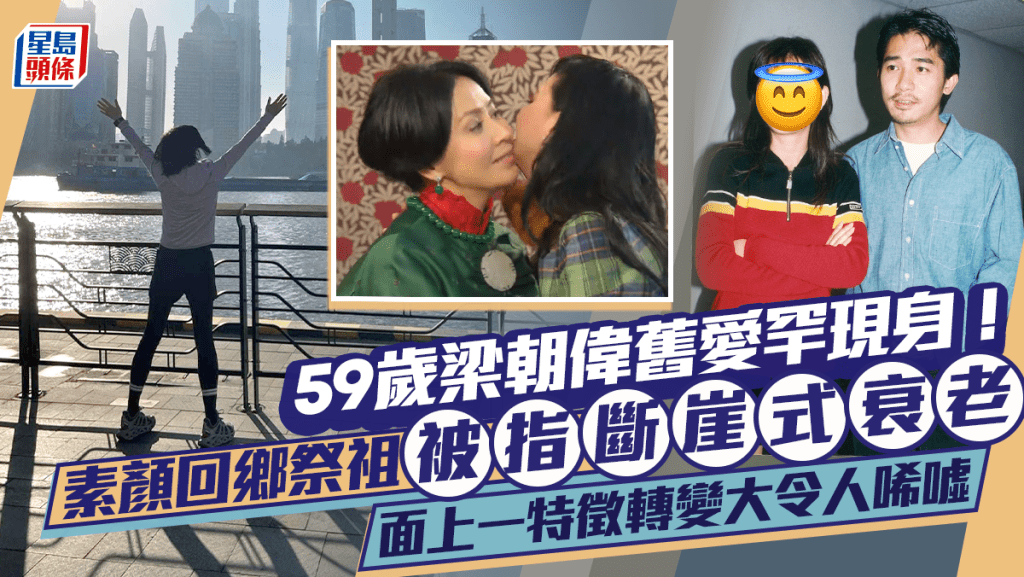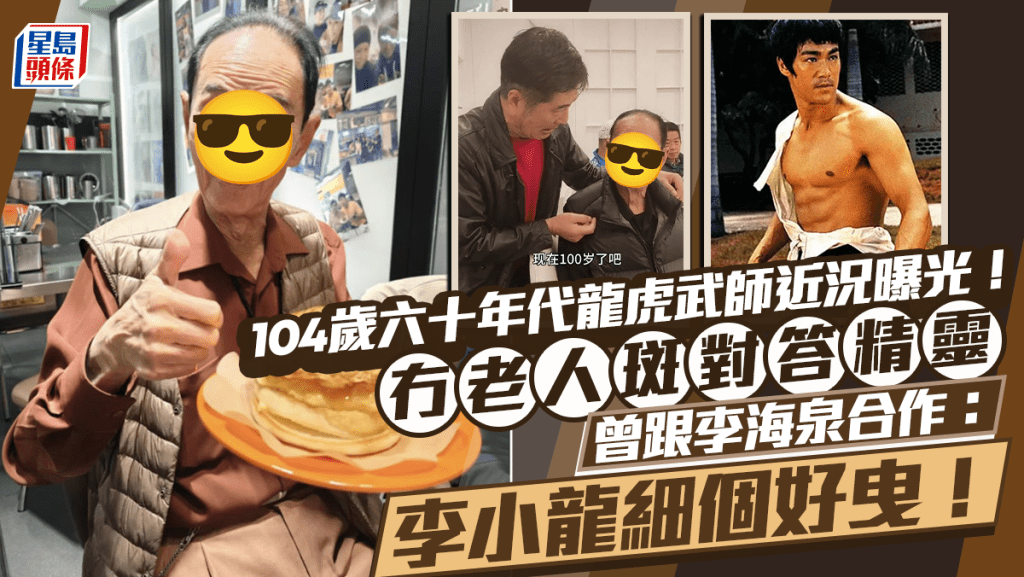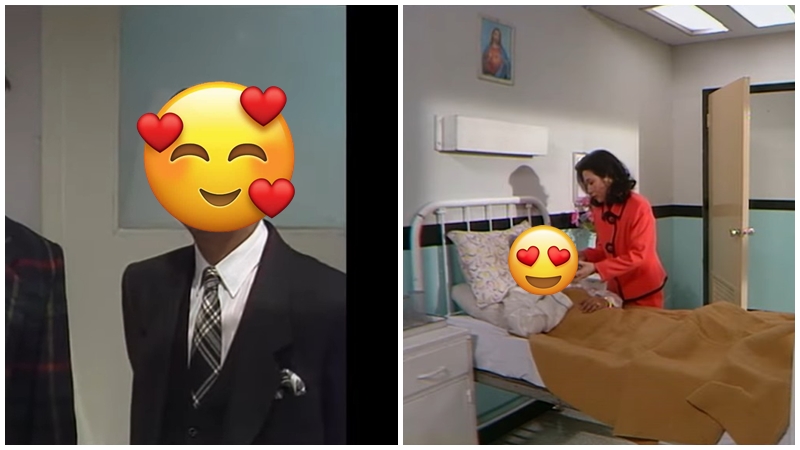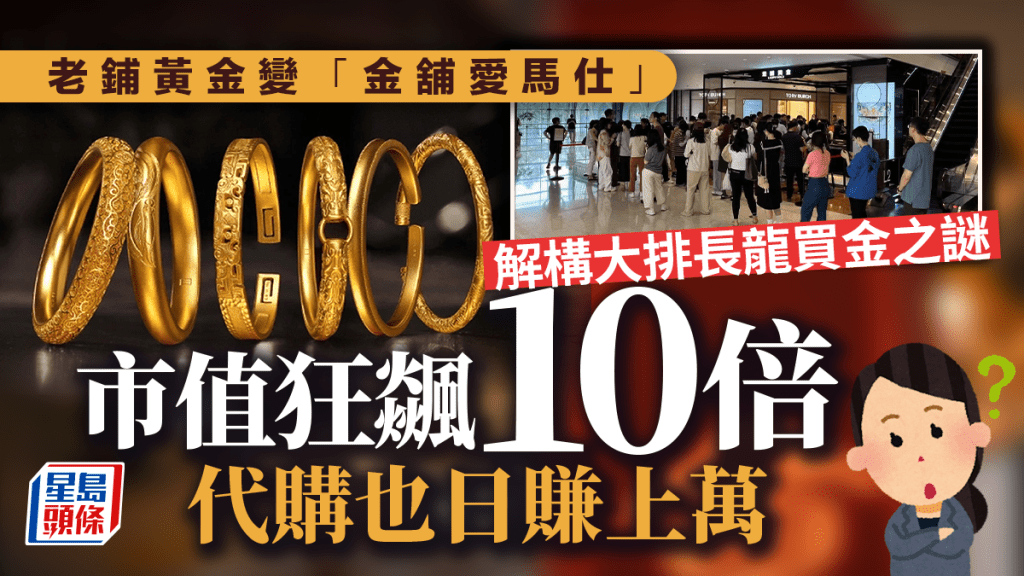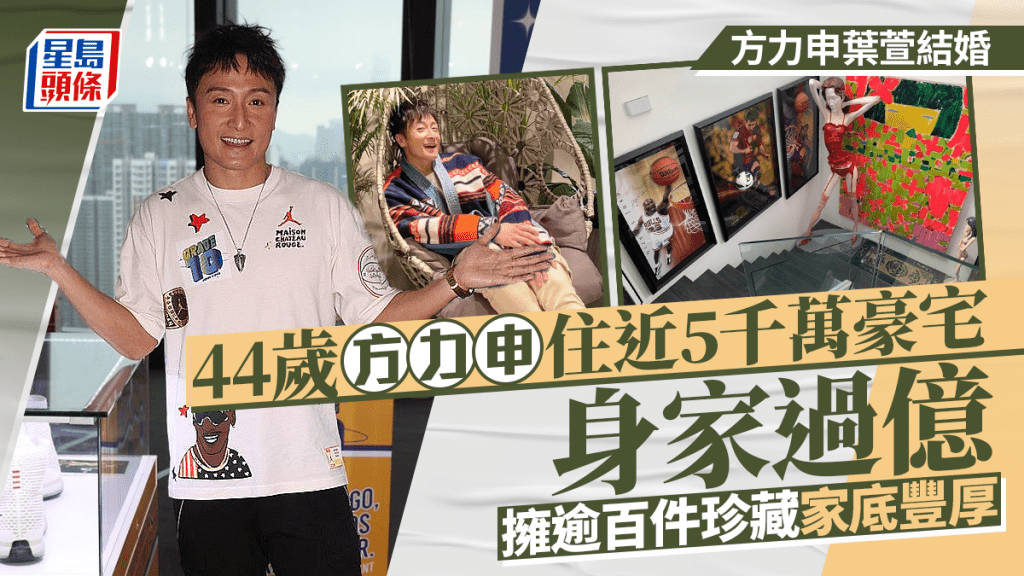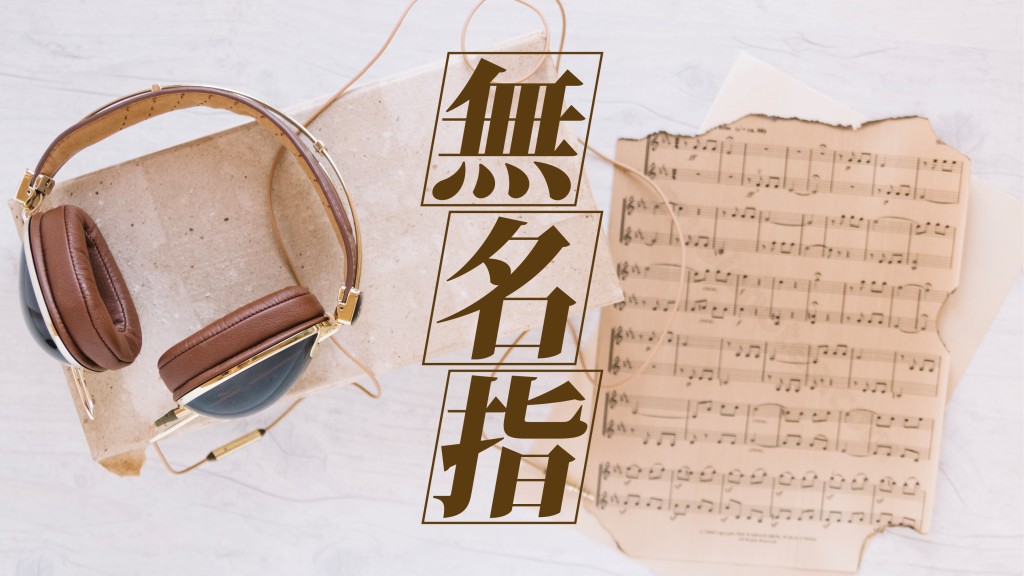譚紀豪 - 漢字文化圈 | 無名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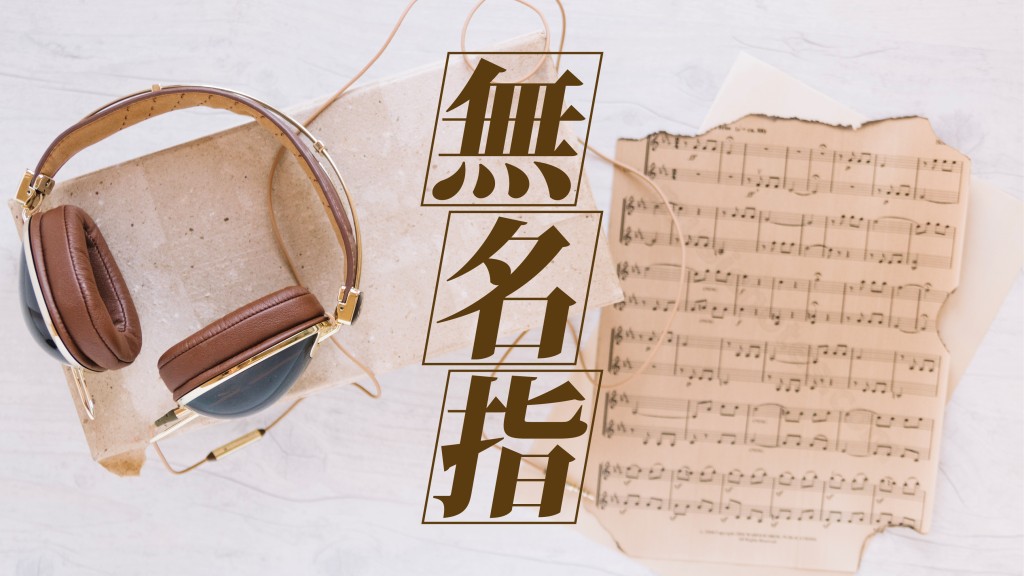
去日本和韓國玩,我有一個不太好的習慣,多數印刷版旅遊資訊,如地圖或單張,我都取中英文各一份,前者知道其漢字名稱,便於記憶;後者了解其拼寫讀音,方便溝通,如富士山叫Fujisan,漢拏山是Hallasan。
當你以為在漢字文化圈裏,「山」都叫san,會有日本人跟你說,「不,山是yama。」我這幾天在京都,和一個旅居日本幾十年的朋友聊起,他說san是「音讀」,yama是「訓讀」。那何時音讀何時訓讀?「沒規則,要看語境和習慣。」我無語。
東京的「京」字是kyo,京成電車的「京」則是kei,北京的「京」又變成kin,「前面一個是吳音,是朝鮮半島傳來的江南音;中間的是漢音,接近唐朝的長安音;後面是唐音,是宋朝以後禪宗傳到日本帶來的福建口音。」朋友娓娓道來,我聽到頭都暈了,「為甚麼唐朝傳來的叫漢音,宋朝的叫唐音?」答曰:「無解。」
上下千年,日文和漢語關係千絲萬縷,從草書行書字型到各地方言讀音,至今仍有跡可尋。20世紀初,中文反過來跟日本學習,新文學運動和後來簡體字演化,日文反向輸出,改變了漢語發展。今天我們去日本旅遊,街上路標和餐廳菜單都大概猜得出7、8成,也是兩地語文千年互動所致。
文字只是面子,裏子是文化。一個韓國朋友說,漢字文化圈內中日韓和越南四地的人思想接近,較容易溝通,我非常認同。其他亞洲地區如泰國、菲律賓、印尼,文化上差異較大,難怪與女傭們溝通總有隔閡。
資深唱片人兼樂迷
譚紀豪
最Hit
59歲梁朝偉舊愛罕現身!素顏回鄉祭祖被指斷崖式衰老 面上一特徵轉變大令人唏噓
2025-02-13 09:00 HKT
104歲六十年代龍虎武師近況曝光 冇老人斑對答精靈 曾跟李海泉合作:李小龍細個好曳!
2025-02-13 12:30 HKT
老鋪黃金變「金舖愛馬仕」 市值狂飊10倍 代購也日賺上萬 解構大排長龍買金之謎
2025-02-14 06:00 HKT